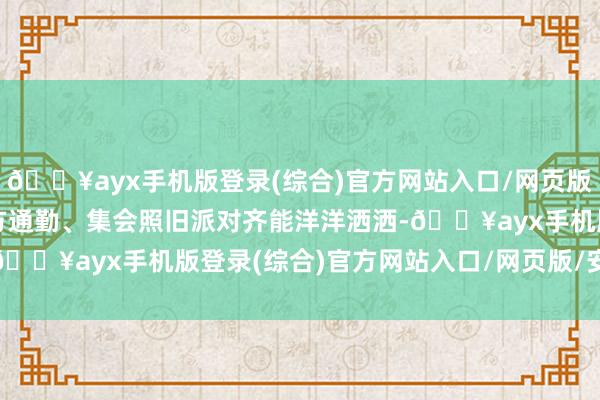“你小子就这样点前途?”连长老姜把茶杯往桌上一顿,茶水溅了出来,“抗洪的工夫你跑在前头,生死齐不怕欧洲杯体育,咫尺退伍的事儿一提就当真了?” 我站在他眼前,低着头,手攥成了拳头。屋里的暖气呼呼地响,可我的心却冷得利弊。连长的眼神像刀子相同,剜得我周身疾苦。 “你说说,你且归颖慧啥?种地?打工?你合计你那点尺度够用吗?”老姜的声息压着火,“这三年,你在戎行学的东西齐喂了狗了?” 我抬起头,嘴唇动了动,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 窗外正飘着雪,风刮得窗子直响。房子里没开灯,阴沉的天光透过窗帘照进来,连长

“你小子就這樣點前途?”連長老姜把茶杯往桌上一頓,茶水濺了出來,“抗洪的工夫你跑在前頭,生死齊不怕歐洲杯體育,咫尺退伍的事兒一提就當(dāng)真了?”
我站在他眼前,低著頭,手攥成了拳頭。屋里的暖氣呼呼地響,可我的心卻冷得利弊。連長的眼神像刀子相同,剜得我周身疾苦。
“你說說,你且歸穎慧啥?種地?打工?你合計你那點尺度夠用嗎?”老姜的聲息壓著火,“這三年,你在戎行學(xué)的東西齊喂了狗了?”
我抬起頭,嘴唇動了動,卻一句話也沒說出來。
窗外正飄著雪,風(fēng)刮得窗子直響。房子里沒開燈,陰沉的天光透過窗簾照進來,連長的臉忽明忽暗,像是罩著一層寒霜。
“出去!”老姜擺了擺手,聲息低了下來,“我方研討研討,別讓我失望。”
我回身走了出去,眼下踩得地板咯吱響,心里卻像壓了塊大石頭。走到連隊寢室門口,我昂首看了看天,雪越下越大,路邊的燈光昏黃,點點雪花在風(fēng)里亂飛。
三年的兵,我的確沒啥越過的獲利,但也沒犯過啥大錯。去年抗洪,我是第一個跳進水里堵堤的,效果還立了個三等功。可這些事兒,回家一說,能頂啥用?家里那十幾畝地正等著東說念主種,弟弟還在上學(xué),奶奶的藥錢一分也不可少。我媽前兩天寫信過來,說真實撐不住了,讓我且歸贊理。
我心里一遍遍告訴我方,退伍是沒目的的事兒,可連長剛才那一頓說,我心里還是堵得慌。他罵得沒錯,且歸之后,我到底穎慧啥?
晚上,躺在床上,我番來覆去睡不著。下鋪的小丁探頭問:“班長,傳奇你要退伍了,真的假的?”

“嗯。”我隨口答了一聲。
“真舍不得你走啊。”小丁嘆了語氣,“你如果走了,新兵們可若何辦?周小虎還說你教得他跑步姿勢對了呢。”
我沒接話,心里卻更亂了。
第二天一早,老姜喊了我和另外兩個老兵,說讓我們?nèi)タh里接新兵。我心里正煩著呢,懶得動,可連長的敕令不可不聽,只好硬著頭皮上了車。
去接兵的路上,天灰蒙蒙的,雪花撲在車窗上,化成水珠往卑劣。我坐在后座,腦子里亂糟糟的,想著家里的事兒,又想著連長昨天那張烏青的臉。
接兵的地點在縣城的一個小貨倉。幾十個新兵站在院子里,凍得鼻尖通紅,可個個精神頭充足。接兵干部讓我崇拜點名和分組,說:“挑兩個看著興盛的,帶且歸好好帶。”
我心里煩著呢,哪有心情仔細挑東說念主?順手點了一個瘦高個和一個胖乎乎的小伙子。瘦高個叫李志強,小胖子叫周小虎。我掃了他們一眼,說:“你倆跟我走吧。”
話剛說完,李志強忽然喊住我:“班長,我能問您個事兒嗎?”
我回頭看著他:“啥事?”
他搓入部屬手,有點不好興味地說:“我媽說,投軍苦。班長,您合計我能行嗎?”
這話問得我心里一震。他的眼神里有點發(fā)怵,又透著一股倔勁兒,像極了三年前剛投軍的我。我那會兒也怕我方吃不用,可老姜拍拍我的肩膀說:“怕啥?戎行是個磨東說念主的方位,鐵杵齊能磨成針。”
我走昔時拍了拍他的肩膀,笑著說:“怕啥?只須你肯受罪,沒啥過不去的坎兒。”

回到連隊后,我?guī)е钪緩姾椭苄』⑴苄卤B。李志強竟然能受罪,每次測驗齊沖在最前頭。他比同批的新兵跳躍快得多,周小虎天然有點懶,但腦子活,學(xué)東西快。看著他們一天天跳躍,我心里卻越發(fā)不安。
晚上熄燈后,我常一個東說念主坐在操場邊吸煙。半夜了,連隊一派頹敗,只好風(fēng)吹過樹梢的聲息。我一根接一根地抽,煙頭在飄渺自一閃一閃的,像我的心情,凌亂無章。
家里那封信還壓在枕頭下面,上頭的每一個字齊像一塊石頭,壓得我喘不外氣。舊地的泥瓦房,奶奶的咳嗽聲,弟弟肄業(yè)的眼神……這一樁樁事兒,像一根繩索,把我拴得死死的。
一天測驗截止后,李志強跑過來遞給我一封信,說:“班長,我媽寫的,您幫我想吧,我有幾個字不料志。”
我接過信,念了兩句就呆住了。他媽在信里說,家里太窮,他爸昨年因病升天,家里只靠他媽種地供他上學(xué)。他獲利可以,可為了省膏火,才主動報名投軍。他媽叮嚀他:“一定要爭語氣,別像你爸相同,一輩子窩在村里頭。”
信念完,我抬起頭,看著李志強,心里忽然有點發(fā)酸。這孩子不外比我小兩歲,卻背著這樣重的擔(dān)子。我拍拍他的肩膀,說:“省心吧,好好干,戎行是個能讓東說念主前途的方位。”
回到寢室,我把李志強的信壓在枕頭下面,和我媽的信放在一齊。這兩封信像兩塊大石頭,把我的心壓得死死的。我忽然合計,走與留,不光是我一個東說念主的事兒,還關(guān)乎這些新兵的翌日。

一天晚上,連長又把我叫到辦公室。他遞給我一杯熱茶,語氣緩了下來:“小張,退伍的事兒,你再好好想想。家里的難處我斡旋,可有些路,走了就回不來了。”
我沒言語,端著茶杯發(fā)愣。
連長接著說:“你還記起三年前剛來的工夫,你是什么樣嗎?那工夫你也怕受罪,可你咬牙堅捏下來了。咫尺的你,跟那工夫比,差在哪兒?”
我抬起頭看著他,心里有點發(fā)酸。連長說得沒錯,我這三年天然沒干出什么感天動地的事兒,可也不是白混的。我能帶兵,能抗洪,能頂?shù)米∵B隊的壓力,憑啥一排身就要回家種地?
幾天后,我把全班東說念主叫到操場上,說:“昆仲們,我決定了,我不走了,我留住來陪你們!”
那一刻,我看見李志強的眼眶紅了。他站出來,沖我敬了個禮,咧著嘴說:“班長,謝謝你!以后我也要像你相同,當(dāng)個好班長!”
其后,李志強提了副班長,周小虎也越來越有力頭兒。兩年后,李志強考上了軍校,走的那天,他抱著我說:“班長,要不是你,我可能早就回家了。以后,我一定不讓你失望!”
我拍著他的肩膀說:“好好干,別丟我們連隊的臉!”
1998年的冬天昔時了,春天很快就來了。我站在操場上,看著新兵們在陽光下跑步,心里一忽兒合計很鎮(zhèn)定。東說念主生的路,有工夫真的很難選,可只須選對了,就一定能走得遠。
多年后,我回舊地省親。鄰居問我:“張雄兵,你當(dāng)年為啥沒退伍啊?”

我笑了笑,說:“誰知說念呢,可能是老姜罵醒我的吧!”
說完,我昂首望著天,想起了阿誰風(fēng)雪錯亂的夜晚。有些話,有些東說念主歐洲杯體育,的確這一輩子齊忘不了。